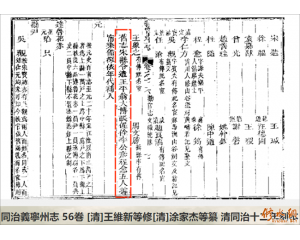那天晚上,朋友亮一连几个电话催促我出门,说他和国、生等朋友在广场喝茶聊天。我说有事去不了,他火了,在电话里头大喊:“是没钱打的对不?你到街上打一辆最漂亮的的来,车钱我付。”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挂了电话。 不到十分钟,我便到了广场。那晚天气不错,广场喝茶的人真不少,亮他们就坐在大灯底下,我快步向他们走去,突然,身后不知何时呼啦啦地跟着五、六个提着木箱的擦鞋工,她们的眼睛不瞧别处,专盯着我脚下的皮鞋。 我这个人做人向来比较低调,我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人,而且是清一色女性,虽然她们衣着不整齐,且每人手中还提着一个木箱,但总有点大人物出入公共场所的味,前呼后拥的,着实让人不安,我不由得冲她们说:“干什么、干什么?不擦不擦!” 但她们可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屁股还没坐下,一个中年短发女子就迅速占领有利位置,坐在我的脚前,短发女子后面还站着几个提木箱子的人。 “叫你擦鞋呢。”亮笑着说。 HULING 我没有理会她们,而是笑着向亮要几块钱的打车费。 “我只请你擦鞋,其他的我不管。”亮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 “擦就擦,捡到什么总比丢掉什么好。” 见我准备擦鞋,短发女子立即从木箱里拿出东西,但是站在旁边的长发中年女子不知何故在短发女肩上拍了拍,示意她走开。短发女子抬头看了看长发女子,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提着木箱子要走。 “这是干什么?”我说。短发女子不说话,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且决计要走的样子。长发女子满脸堆笑说:“我来帮你擦鞋。” 我终于看出了名堂,这不是欺负人啊!我手指着长发女子,一字一句道:“我不要你擦。”然后对短发女子说:“你来擦!” 长发女子见状,提着木箱子尴尬地走了。 在短发女子帮我擦皮鞋的时候,我才仔细打量,她穿着很朴素的花格上衣,瘦瘦的脸上留下了些许岁月的痕迹。 “那女人怎么这样欺负你?”我问短发女子,她看了看我,不说话。 “嘿,她是个哑巴!”亮喝了一口茶告诉我。 HULING “哑巴?!”我一惊。 很快,鞋擦好了,我拿一元硬币丢到哑巴女子的木箱里。突然,哑巴女子从木箱里找到那一元硬币,放到我喝茶的桌上,微笑着摆了摆手。“这怎么行?”我自言自语道,我注意到,她的眼里满是感激的目光。 “拿着,这是你的劳动所得。”我说道。 哑巴女子执意不要,提着木箱便走,我急了,追上前去,将一元钱丢在她的木箱里…… “她是在感激你呢。”亮依旧笑眯眯地说。 但我却笑不起来,心中隐隐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擦皮鞋的哑巴女子是出于哪种目的不要那原本属于她的一元钱。一元钱对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她,却是整天提着木箱低三下四,满街奔波,甚至是与他人“抢”来的。 我想,这一元钱,已经超出了它原本的价值。它是一种生命的感恩、一种人性的还原,一种被欺负后深层的唤醒,一种碰撞后痛快的释然。 如今,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哑巴女人依旧在擦鞋,只不过擦鞋的地点从广场移到了马家洲,与十多年前相比,她苍老了许多。每次喝茶擦鞋,我都会等待着她的到来,不为别的,只为那年的一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