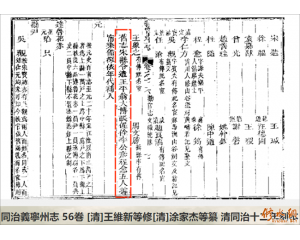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
听着民俗介绍,我有时觉得很遥远,有时又觉得很贴近,仅仅咫尺之遥,就在他们的唇齿之间。这是因为,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 日出东方一点黄,娇莲出门洗衣裳;手拿年棰轻轻打,下下打在麻石上,一心想着我的郎。 好不动人的“一点黄”!没有矫饰,更没有造假,它确实是早晨的嫩嫩的太阳,和娇莲一样质朴清纯的太阳。由此,我怀疑在一些影像里,会不会有人拿着落日冒充朝阳。他们的太阳怎么会那么红呢?红得好像抹了唇膏。 洗衣裳的娇莲令爱唱山歌的修水歌兴勃发。又有朋友忍不住了。他歌唱的时候肯定把我们当作一架架山峰了,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动情——打个哈欠泪汪汪,今日么事咯想郎;昨天想郎挨了打,今天想郎受了伤,眼泪未干又想郎。 爹呀娘呀,嫁女嫁到朱溪场,一床被子一只箱,箱子里头空光光。怪不得爹也怪不得娘,就怪那媒人烂肚肠…… 这位娇莲还没出门就胳臂肘往外拐了,她令在座两位小青年,兴奋不已,他们不断插话介绍本地风情。当时忙着记录歌词,我竟忘了该请他们唱一段的。我相信,他们也能唱。我想起六年前第一次来修水,和一群诗人泛舟湖上,有几位当地的青年诗人你一句我一句唱起修水山歌,不料想,岸上竟有山民和船上的陌生人对起歌来。后来登岸上山,见一中年男子赶着牛迎面而来,已擦身走过了,大家才恍然,想必那山歌手就是他了,赶紧喊住他,要他单独唱一支听听。我记得当时他侧脸望了我们一眼,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答应,牛依然顾自前行,他仍是悠悠然紧随其后,这时,他仿佛是牛的仆人。但是,他还是唱了,不为邀请,不为听众,只为他的牛和他的山。所以,他唱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 修水网 那粗犷而真挚的歌声忽然打破了深山里的寂静,当远处依稀有三两声鸟的回应时,歌词对于山歌就显得不重要了。我想,他的歌声里大约也会有一位娇莲吧? 凭着对那位放牛汉子的记忆,和生活在县城里的修水朋友对山歌的记忆,我敢说,尽管时过境迁,在爱唱山歌的修水,山歌仍健康地活着,也许它只是偶尔飘出口中,却久久地回荡在许多人的心头。在民间艺术芳菲已尽的今天,修水山歌真如躲藏在林中、俏立于崖畔的一树树桃花,分外惹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