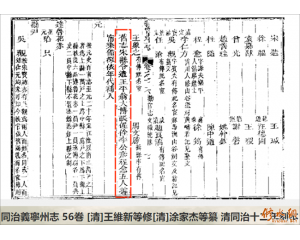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
在修水跑了两天,也没见着稍大些的平畈,前后左右的车窗尽是山景,蜿蜒曲折的道路总有河溪相伴。时值仲秋,从山下往上看,山腰上层层叠叠的梯田,长长短短的金黄色,在坡面上画下规整而富有变化的直线,像五线谱,或者简谱上的各种符号,而零零落落地散布在山坳里的村舍大约就是一个个音符了。 听说,在修水乡间,若是客人上门来了,夜晚无法安顿,主人会索性搬出山歌铺开来,一半作床,一半为褥,就这么彻夜唱歌,陪着客人欢乐到天明。他们的心躺在歌声里,同床共衿,相依相偎,盖的是歌声,枕的也是歌声。我把他们的歌声想象为我幼时见过的旅店里的大通铺,或者,是我中学时代下乡学农睡过的打在祠堂戏台上的地铺,垫着很厚的稻草,拥着彻夜不眠的兴奋。我想他们的歌声一定是用本地多有种植的某些植物的纤维织成的,比如棉花和桑蚕之丝,能御寒,而且温馨。 xiushui.Net 我忽然热衷于寻访那些岌岌可危的民间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浸润其中的浪漫情怀感动了。感受着那些来自民间的乐声和舞步,我发现,有了它们才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生活的本相。哪怕苦难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呻吟和喘息;愉悦自己,似乎原本就是一种生命本能。所以,即便是呻吟和喘息,也是可以被赋予旋律和节奏的。而且,地处幕阜山区的修水指着苍茫的历史深处告诉我,愈是在孤独的贫困的环境里,人的愉悦自己的本能表现得愈强烈。譬如,我到过的金盆村,沿着山沟里的垄田散落在两侧的山弯中,最大的自然村怕是也不过三五家,零零落落的房屋一直绵延到深山里。这种松散的居住状况大致反映出原始的生产形态。可是,恰恰在这里,我领略到一种叫“十八翻”的打击乐,它由鼓、锣、钹、镲及唢呐等乐器组成,为我们演奏时缺了唢呐,也有六位乐手。是不是孤独而浪漫的心聚集在一起,相互敲打,才有了十八种变化的锣鼓点子? 想来,当先民们举家迁至地广人稀的幕阜山区,垦荒造田,休养生息,他们的生命就和山里的一切息息相通了。唱不尽的山歌,大概就是唱给重峦叠嶂听的,唱给林子里的警觉的生灵听的,唱给自己的屋舍田园听的,而他们自己则陶醉在大山的回声里。 内容来自xiushui.Net 新打禾镰丁冬滴答,总磨总白总放亮,这么大的姑娘怎么这么不联郎。联郎莫联奉新担脚贩,联郎要联宁州老表会写会算会讲会哇榜眼探花状元郎,一夜风流到天光。 虽然,歌手长得瘦瘦小小,其貌不扬,但是,他自豪的歌声,得意的表情,一定和历史上宁州老表的儒雅风流有着血脉渊源。也许,相传至今,仅存那股气韵了,然而,它却依然生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