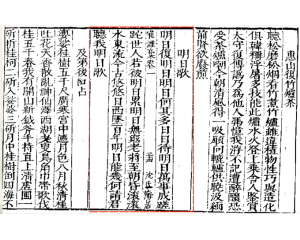|
寻一座城,与你(组诗)
钱轩毅 复活的鹦鹉街 比起凤凰涅槃,我更相信鹦鹉的复活 在南山隔江守望多年,陷入沉默的石头 坚硬的内心一直居住着一座城池 太久远了,非虚构的黑白底片被重新傅彩 透过一排排油纸伞,青灰色砖墙行走的光晷 脚步软下来,自风味小吃店云纹窗棂滑落 阳光嫩黄,依旧是老配方,老味道 老人拄着手杖,小孩举着糖人 喜欢玩自拍的女孩,接连换了几个pose 着古装汉子从大酒缸舀上一盏陈酿 一仰脖,十八巷桃李春风 把自己放进人流,交给一条重生的街巷 左边不时走过唐人,右边不时走过宋人 脚下的青石板,把过去与未来铺贴在一起 陌生人视线相碰都满脸含笑 却不相互打听名姓,他们爱着各自的幸福 “吃碗茶噹——”,一个人巷头喊一声 一个人巷尾回一声,鹦鹉翅翼扑棱着黄昏 一千多米街道,每一寸都是你我的故乡 跨鳌桥 “旧有石,嶙峋兀立,状若鳌头,遂以名桥” 本文来自修水网 一块顽石不虞被赋予新的意义 跨鳌桥,一个神性的名号连通两岸 大多人和我一样,仅知它的诨名“王亚桥” 像偶遇儿时的伙伴,绰号脱口而出 愣是老半天想不起他的名姓 并不妨碍,背着笈囊赶考的书生,跨过它 白莲教由楚进入州城,跨过它 太平军与湘军厮杀,跨过它 北伐将士扛着旌旗,跨过它 ——几百年后的这一刻,我正跨过它 桥身青苔的暗绿,掩藏了刀光剑影 汩汩鳌溪水,稀释了汲汲功名 通远门马头墙的翘角,无限接近天空 连接跨鳌桥的山路,无限伸向远方 古城的犀津桥、状元桥、鹦鹉桥…… 都苍老在县志中,剩下些发黄的虚名 唯有跨鳌桥,它先于你生,也将后于你死 桥头,满汉茶楼店幡,轻摇着过往的风 你就着菊花茶,看鳌水缓缓注入修江 鳌石深埋于沙砾,桥下悠然而过的桨橹 无人知晓已摇向何处 寻一座城,与你 着短襦的女子,在西茗河捣衣 赶考的书生经过跨鳌桥再也没回来 平平仄仄的城墙砖,至今说着宋语 xiushui.Net 一个从老城走失的孩子 站在多年以后的犀津渡口 回望走失多年的老城 一声号子从东门穿过来 从西摆穿出去,融进修河左岸 那些险被推平的时间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站在巷子尽头 举着一串紫红的糖葫芦 正是人间清晨,日出时分 爱一座城,就用一场雪 马头墙离天空又近了几寸 老巷,老井,老祠堂 旧爱,旧痛,旧时光 五瓣梅香托住雪,一如千年前 肖家巷弹棉花的弦响,雪的光 把爱过的人和事重新爱一遍 举轻若重的白,茫茫渺渺,没有尽头 爱一座城,就用一场雪 从凤凰山顶到城墙根,不挑拣落脚点 实在爱不动的时候,煨一盆碳火 煮雪。雪化的水汽分娩清澈的薄光 逝去的油纸伞得以湿漉漉重生 一切都在。天井明亮处,姨奶坐在那糊伞纸 她养的小黑狗,追着窗玻璃反射的天光 吠几声,然后不停地抖落身上的雪花 月光,照进宋的土层 必定是出于无意,用一层盖住另一层 用一个朝代盖住另一个朝代 HULING 必定是出于无意,城门口的月光下探数米 宋元明清叠压在玻璃后的狭小空间里 必定是出于无意,土层颜色不一的肌肤 被折射的光针刺青 砖瓦、瓷片、秤砣、铜钱、炉灰…… 这些老派风格的写实图纹,均年迈于我们 必定是出于无意,墙基被人拿走了城墙 叫卖声、车马声、锣鼓声、厮杀声 老人梦呓声、情人低语声、婴儿啼哭声 在不同的熟土层拥挤磕碰 必定是出于无意,在一个没有我们的时间 埋进骸骨、硝烟、文字、闪电 悲喜与隐闵,日出与日落,荣耀与不耻 对世界欠的债,在人间受的罪 必定是出于无意,月光照进宋的土层 埋土的人已经走了好久 在他们的时间里,和影影绰绰的人影遇见 你不认得他们,他们也不认得你 在河边 我坐在西茗河边的卵石上,太阳坐在 西边的山头。水面游走的光斑 跃动着脊背的锦鲤,抢食我投入河水的 身影。风,在岸边梳理芦苇的白发 如果河水不再流,太阳就会坐在山顶不走 那只捕食的水鸟就会插入水中不出来 内容来自xiushui.Net 我就会把时光凝固为满滩卵石 再安静些,就会清晰听见 祖母在上游浣洗被服的木杵声 梦里那口井 是一口老井,比井砖的青苔更老 比井底的鱼儿更老 比过世的祖父还要老 童年的我,放学就要到井边呆一会 看斜阳自宽大的芭蕉叶间投下 红鲤鱼的影子悠悠游进我的影子 大多时候,星星不来井水中游泳 夜就不敢黑。就像我,离开家乡三十多年 今天不来井口照个影,就不敢老去 如今,水龙头拧开新的生活 井旁青石板上没有了往日的喧闹 老井像失去婴儿的母亲,乳水溢出 无人吮吸的哀伤,湿了垂下的箬叶 井水养大的乡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 当年那些孩子,也天各一方。知否 烟波浩渺的江湖再大,也大不过梦里 老井迟暮的眼神 在秋收纪念馆 一声令下,铁耙、锄头、柴刀、戗棍舞动 这条山路上,许多庄稼一样的汉子 擦了擦脚上的泥土,告别了 他们侍弄的稻谷、大豆、玉米、红薯 告别了他们的父母、婆娘、子女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他们不再收割庄稼,只收割王朝 就是这群收割者,将手中的镰刀 绣到旗帜上,将贫血的年华绣进红的信仰 将自己,一锤子砸进波澜壮阔的历史 将一个旧秩序,砸碎并重组 给梁幼陶* 一个熄灭的老式熨斗 搁在不同花色的布料间 扒开高过头的茅草,青石碑上 我们辨认出这个名字——“梁幼陶” 量体裁衣是他强项,最后这一尺子 显然不是他自己所为,显小,不合身 眼前这匹春光,才应该是他的手艺 瞧,雨点缝出的针脚那么整齐 除了衣服,他一生没做过什么显扬的事情 最好的针线活,是那面旗子 尺寸刚好,够着九百六十万山河 (注:梁幼陶,江西修水人,裁缝。1927年8月,他缝制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凤凰山的传说 你应当首先听见凤凰的嘤鸣 然后,见她从胸中呵出雾海汪洋 滚圆的朝阳卡在喉咙,轻轻一咳 便点着了天火。于云彩的烈焰中涅槃 凤凰,一点点变成凤凰山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她的长喙,化作明月湾一捧流泉 她的羽毛,化作东岭十里桃花 她的骨骼,化作八十万乡人灵魂 她的第一声长鸣滴落北宋 被双井的一位黄姓少年捡起 甩出一个漂亮的传说,从一口井飞入 另一口井,飞出一颗璀璨天王星 她的另一声长鸣滴落晚清 润泽了陈氏整本家谱 五个响亮的名字开花拔节 长进中国的近代史 她的最近一声长鸣滴落今夜 似星子穿行于山城九井十八巷的脉管 谁用豪气点星为灯,蘸着星光磨墨 在新铺开的宣纸上,栽下梧桐 三横四纵,挥笔写下可触摸的憧憬 我从画中的留白处出发,只为 寻找一个涅槃的传说。我的心脏太小 安放不下中国·江西·九江,仅够安放下 一座凤凰山。这里,到处是我的乡土和信仰 山路走着的,山间睡着的,我、我们,都是你的子孙 我们在登山,山与春秋与我同在;我们在续写传说 八十万人的天色如此辽阔。头顶,又一颗星突然闪亮 修江两岸,次第万家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