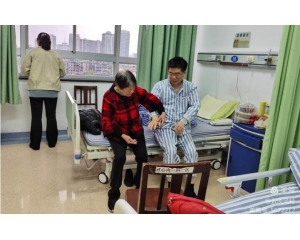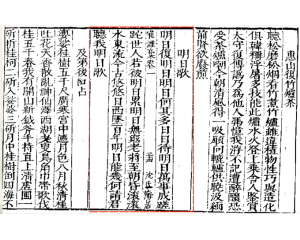|
在九江师专就读的时候,我很少近距离接触老师。 大一,我总是在街上一个人游荡,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颓废、也许是为了寻找。大二,我主要偷偷练习写作,咀嚼书本、反刍生活;到了大三,青年男子的诸多问题来了,学生味就少。到最后,也没留下什么师生间的故事。  他评我的论文为“我喜欢”,认为这种用自己的话语写自己感性认识的论文,即使理论水平不高也是应该肯定的。我把我的习作本交给他看过,他在扉页写了满满一页寄语,教我怎样认识文学,鼓励我坚持写下去。 我们那届毕业,工作不再分配。我经历两次高考落榜,经历父亲病危时进考场、父亲病逝时填志愿等黑色时刻,才得以考取大学,又是靠妹妹打工供养才完成学业,读书一场空本已无法交代,再添无处安身的现实压力,境遇可谓暗天黑地。 修水网 2001年初在深圳碰得遍体鳞伤后,几近成为拾荒的流浪汉。所幸那时的火车可爬,我躲在火车的厕所里回到了九江,找到98级学生戴洪贺三里街租住的房间。我这个老乡后来描绘了我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个细节,说我从包里掏出僵硬了的半个馒头,一边叹气一边丢到垃圾桶里。 不久,不记得从哪里终于弄来了一点钱,在九江师专对面五里街铁道旁租了间民房,以米饭和小葱拌豆腐为生,妄想靠写作挣稿费——日日苦思冥想,夜夜写字涂字。 这时,李宁宁老师找我了,我还在交往的女朋友还坐在他的讲台下听课。由她传话,他叫我去了他办公室。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在九江了,也许是我与校园环境不搭调的惨淡身影某一次被他看到了吧。 我战战兢兢进了他的办公室,原来他找我是安排我去九江日报社实习。他见我的时候,平日和善的脸色异常和善,没有多说更没有多问,没一分钟就放了我出来。他叫我直接去找谁谁谁,说他已经说好了。 从此,我在母校出没、在斗室写稿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和理由。后来我并没有实习多久,大约一个多月吧,但现在看来,老师此举意义非常。这是在我的困局里为我开了一个口子,使我不至于没有光亮,不至于滑入自设的陷阱。 HULING 在最低落的时候,我没有游离社会,没有游离生活,没有完全丧失青年男子的尊严和希望,李老师为我操了父亲般的心。我记得,2001年5月1日的《九江日报》上,有我采写的报道《五一节,九江人怎么游》——这于我是一篇比处女作还重要的文字。 在那段特别困顿迷茫的岁月里,李老师在文学上也极力鼓励我、扶持我。一天,女朋友又找到我,说李老师叫我去。去了才知道,他要带我去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我现在还记得,是一起打车去的,会场是老市委里面,研讨对象是《肖士太故事集》。我不是他的助手,也不再是他所教班上的学生,他带我去没有正当理由。 那时我栖栖遑遑,一定神情沉郁,举止惊慌,会场上只会给他丢脸。他带我去,是怎样一种考虑?这一细事于我是重大的,现在想来,仍次次暖到心底。 此后没多久,我把握一个机会离开九江去了北京,生活境遇开始改善。此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按照李老师“我喜欢”的写作路子走了下来,即用自己的话语写自己的感受。 我去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的主要精力要集于求生活,集于缓解社会加诸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一旦生活给了我作品的种子,我就会匀出心血、浇出花来。”在这两方面,李宁宁老师对我的帮助之大、影响之深,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放到我当时的情境中,他每一句话语都是沙漠里的一杯水,每一个眼神都是黑夜里的一盏灯。 HULING 2002年8月底的一天,我从北京回修水赶赴教职的途中,路过九江,到李老师的办公室小坐了一下。临行时,老师送我出来,分开了很远又叫我回去,说要回办公室给我伞。天空虽乌云密布,我觉得雨还远着,又要赶车,就执意不回。 当看到老师迈开步子上楼去了,我跑了回去,只见他在柜子里翻找。“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了?”老师喃喃自语。最后,他红着他那白皙的“书生”脸,说,你就拿走门边那把吧。那伞撑着凉在那里,伞骨有一处软了,伞布底色淡红,点缀着白色的梅花。 说实在的,这种色彩的、破的伞,我实在不想拿。老师见我没动,就亲手把伞收起来,强塞给我。很快雨就下起来了,一路上,我没受被淋之苦。 这次离别后,好多年没有见到李老师。那把伞,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用着,记得石坳中学我宿舍房的门后,它经常静静地倚立着。后因工作调动数次搬家,不知它哪里去了。 李老师如果读到这篇文字,估计会一脸愕然。这些往事都忘记了吧,李老师?其实,我最想问您的是,把伞给了我,您那次下班是怎么回家的,被雨淋了没有? 修水网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樊专砚:男,江西修水人,修水县委宣传部干部,《古城旧梦》特约作者。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