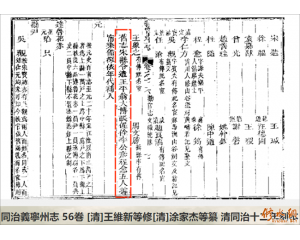我读小学时,学校栖居在孔家祠堂,可能是托孔圣人的福,这个祠堂面积比其他祠堂要大好多。最早时大堂上供有孔夫子的木雕像,上下左右都是很大的厢房,中间两个天井,采光也相当好。
 可惜好景不长,大概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全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判“三家村”运动,小学生也不上课,开始在校园里写大字报,整个孔家祠堂变成一个灵堂样,一片白色笼罩着学校。 后来到了五、六年级时,学校就不发了课本,只是发一本毛主席语录,学生千遍一律每天读诵毛主席语录。老师也不教什么。 这时我所结识的学校之外的第一个文化人,是我们村的一个道士。他家和我家住得很近,晚上经常到我家和我祖父聊天,我特别喜欢听他讲古,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等章回小说。每每听得津津有味,总是不愿意去睡觉。 修水网 我母亲知道他因为长期要抄写道士经章,一手小楷写得好,便求他教我写毛笔字。后来还教我做对联,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还给我讲了一副经典对联,“玉帝巡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龙王夜宴,星灯月烛,山肴海席,地为盆。”这对联几十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 虽然我由于手比较笨,直到很大后,在书法上都没有什么进步,但对于国学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由此我开始特别喜欢看古典小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位“老师”被冠上坏分子的帽子经常拉出去批斗,我只能站在台下无奈地看着。后来他怕对我家有影响,也就不太来我家了。 那时记得乡里最活跃的就数手联社,它的全称叫手工业联合社。乡下称他们叫手艺人,有裁缝、铁匠、木匠。他们组织了一个业余剧社,每到秋闲时经常会演一些古装戏,这里面数裁缝的文化好些,主要由他们唱主角。 我总喜欢到后台去看戏,虽然年幼不太懂。 HULING 我的小伙伴也是我的书友,他比我年长约两三岁,由于他父亲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我的这位小伙伴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他的父亲就是我所崇拜的剧社中的一位裁缝,不是因为他的手艺好,而是因为他是文化人。特别是国学方面有一定造诣,直到前几年我还去他那里讨教过易经方面的知识。 虽然我还在上学,但也是半工半读,一星期只上三天课,三天劳动。他家离我家只有半里路左右,每逢星期天我们就经常一起借书看。 到我读完高中后也没有了书读,虽然我很想读书,只能下放到生产队劳动。这时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交谈、探讨,虽然那时的文化园地是一片荒芜,但我们却依靠四处借书来填补没有书读的空缺。 夏天,在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便会坐在小河的木桥上,有时谈着各自对某本书的看法,有时会就当时的景致题诗作对,以抒发自已苦恼又无奈的情怀,直到我参加工作离开家。 有一位小学老师解放初曾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人很敦厚老实,假如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假使他没有那份野心,他也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也就没有后来的十年沦落为阶下囚。 本文来自修水网 造反派夺权时老师做了回先锋,当时很是趾高气扬,占领了公社的办公室,将当权派扫地出门。后来他在公社门口的墙上,写一幅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这标语先用报纸写好字履到墙上,再用红油漆加上,就算成了。 可是在写字时没有发现报纸的反面有毛主席和林彪的像,履字时用原珠笔在像上划了两笔,按现在来说这本来是无意的,但当时可就是天大的问题。 如果当时这张报纸毁掉了也没事,偏偏这位老师将报纸保留在办公室,偏偏又有这样好事之人,拿着这份就报纸去区中学的红卫兵那里告状。当天晚上老师就被五花大绑推上主席台批斗,第二天就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放在学校里监督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恢复他的教师资格。 在那个时期,我还认识一个郭姓裁缝,他本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因为脾气耿直,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单位开除工作下放回家。生活所迫便请北京的同学为他买了一本裁剪法的书,自学成才做起了裁缝,也算是混口饭吃。 但这个书呆子经常会闹些笑话,如有人说他做的衣不合身,他说我是照书做的,书是国家印的你去问国家,搞得人家哭笑不得。 xiushui.Net 那个动荡时期师资力量青黄不接,很多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在教中学,他看到这个情况,还会去讥讽那些老师,说是你们这些“鼻涕虫”都在教中学了,真是不怕误人子弟呵! 那个时期我还亲历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村里有位老人去世,开个追悼会,生产队长致悼词。他说:“最高指示,某生产队某某人死了,本来今天这个话是要他来说的,我代表他来说两句……”话一说完引来哄堂大笑,会没法开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破坏文化的闹剧,有文化的不能施展才华,没文化的又不能学文化,人们都是在瞎胡闹。好在这场闹剧在人们理智的自我捡讨中结束了,历史对这场运动带来的祸害也早已有认定。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徐晓明:男,修水县上杭乡人,修水县检察院退休干部,一九八七年任《修水县商业志》主编,参与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