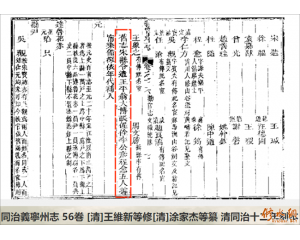今天去,却是墓旁树木成阴,早过了“墓有宿草而不哭”的时候。 虽我和外公相处的时间不多,多是随着父母去做客,或暑寒假去住些时日,但外公对我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一直卧病不起。每次去,我们进门先到床头和他打招呼。他从被子里翘出上半身,消瘦苍白的脸上堆满亲切开心的笑,精神好的话,还会伸出他嶙峋的手,摸摸我的头。临走前,又到床前去告别,这时他总是目光温润,话语低缓而有力,说些教导性的话、鼓励性的话。 我现在想不起那时他说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躺在床上推敲了很久甚至我呆几天就推敲几天的话语,一定是字字扣理,句句暖心,一定春风化雨地催促着我成长。我和小伙伴在屋外玩耍,其实他也会细细地听——因为有时他会喊我进去,纠正我的言行。 我的名字是我外公取的。据说当时原想随便叫个名字算了,那时农家的孩子只能世袭农具;但外公后来还是用意深远,给了我“专砚”两个字。不知不觉中,我有了专心于笔砚的志向,并在名字的暗示下,越来越坚定。 内容来自xiushui.Net 读高一高二的时候,我被现代诗迷住了,例如汪国真、席慕容,把英语和数理化全抛到了脑后,自命为“校园诗人”,自信于诗歌未来。外公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医院的病榻上与我谈了一次。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谈话的其他内容我没有记清,但主要意思一直指导着我的人生选择。他说,古代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有职有闲、有衣食保障。我明白了我的处境后,立即收起青春的狂妄,开始了艰难的高考之旅。 大学毕业后,在外务工两年,找到了一条很好的从商发财之路,但我后来还是毅然选择了一个清贫清闲的职业。现在我的职业以笔耕为主,业余也有一定的时间和状态从事文学创作。可以说,我的笔砚人生,是外公开启和指引的。 外公姓张字振汉,号张翎。翎,是鸟翅膀或尾巴上长而硬的羽毛。外公也人如其名,晚年的十多年虽一直躺着,仍张着他的“翎”。我从长辈那里略知一些他的经历。外公年轻时是一个气宇昂扬的教师,在学校里仗义执言,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老家一个偏僻山村为农几十年。因为带着“右派”的帽子,抗凌辱和谋稻粱,使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他养育了六个子女。 在他的床头,有一个立柜,橱门上有他题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的词,《我傻也好(浪淘沙)》:“人欲比天高,富贵思潮,萦神君子大酕醄。傻士偏安寒伧景,稳渡波涛。”词的内容透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孤傲与悲凉,仿佛在提醒自己要明哲保身;但细看其墨迹,却遒劲而洒脱——纵横和坚挺的气度宛然可掬。他的精神其实没有偏安,他的言行依然在“得罪”人。 修水网 www.xiushui.Net 外公家地处那个自然村的中心,窗外正是两条路的交会处,从来往的人那里,总能听到各种闲言碎语。听母亲讲过,有时外公会把村里的某某人喊进来,其人莫名其妙,来到病床前,才知道是领受外公的训导甚至指责——他已经听出了窗外的对错是非。他不但没有不闻窗外事,还管窗外事,即使窗外人比他年长辈尊,该骂的还是骂。 外公“毁于”年轻时仗义执言,满腹诗书地在田埂上失意了一辈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仗义执言,即使到贫病交迫的寒伧晚年。这种秉持道义的底气和勇气,就是知识分子的魂。没有这个魂,怎么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常常这样警醒自己。 躺着的外公,有他的立柜。外公一生只公开了两首诗词,都“发表”在他的立柜上。立柜的两扇门就是两个版面。一个版是刚说的那首《我傻也好》,另一个版是一首叫《油刷时偶占五绝》的诗:“橱柜无珍物,褴褛与杂渣。开门张目看,随手应心拿。”其实,外公的立柜里不是没有珍物,而是珍物太多,有的还是幻化为褴褛与杂渣的人间珍奇。 从他的立柜里我领到了很多很多。 从坟头望去,春山翠涌,春谷花香,二十年的春光年年如是。我暗下决心,我也要修造一个自己的“立柜”,立于自己的身边,即使身体倒下了,仍留“随手应心拿”的人生境界。 本文来自修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