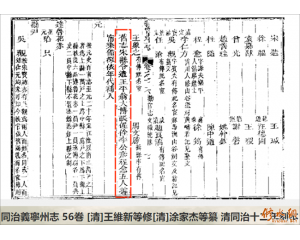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
达•芬奇在论绘画与诗时说,“在表现言词上,诗胜过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过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似乎是连理枝,惯有着某种内在的隐秘的连缀,谁也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 斯画如诗,曹渔的山水画带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观看他的画作,犹如吟诵一首首精致而又意蕴丰富的古风,有着高远的意境和无穷的想象。他的线条是疏简的,就像诗歌中朴素无华的言词,见着朴素,阅读时却呈现了别样的精彩。既是内心的,哲学的,又是外部无处搜寻的,有着山峰一样的精神高度。我喜欢阅读诗歌,更偏好精美的短诗,那种富有张力的语言,奇绝的想象,构成了一个辽阔无垠的内在空间,让人咀嚼,反刍。我尤其喜欢曹渔的山水小品,一幅小品就是一首五言或七言的绝句。曲直变幻的线条就是他的诗歌语言,独特的造形就是他的诗歌意境。他在以画为诗,称得上是个山水田园诗人。如此,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揣测,他在以诗为画,他的绘画灵感来源于诗歌。 南朝宋画家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里说:“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曹渔在纸墨间开拓了一个有别于当下现实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源于古风时期的,是农耕时代的文明世界。那横卧的舟楫,那独立的垂柳,那流动的鸟影,那风动的苇草,那静守的亭台,那孤独的月色,牵引着人走进画中风景,却又永远无法抵达。那流露着怀旧色彩的田园,那月光下清幽的水波,仿佛前朝时期的草庐,那是一个令人惆怅而又感伤的世界。它们都不复存在了,被当下这个嘈杂的世界覆盖了,掩蔽了。多想到那样的月下漫步,多想到那样的水波上逐水漂流。山静,水幽,月清。只有一个笃静的画家才能描绘这样一个淡定的世界,他必定有着“林泉之心”,必定又是“烟霞之侣”。他的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他的世界是理想化的世界,必然也是孤独的世界。曹渔的画中“人”是缺位的,或者说很少出位。可注目他的画作,却又感觉到“人”无处不在,那孤崖上临风而立的树木是“人”,那静守河湾的舟楫是“人”,那飞鸟是“人”,那月是“人”。那草亭之下似乎藏着无数个“人”。每根线条都是一个“人”,每个造形都是一张特殊的脸谱。他的“我”无处不在,他的“人”无处不在。他的内心沉情于笔墨之上。 本文来自修水网 曹渔的山水画除了清幽之气外,还有着萧瑟和孤倔。如果在农耕时代,或许一个兼有陶渊明和陈子昂之性情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他谈画论道的挚友。我非陶渊明,亦非陈子昂,这么任性地推测并没有贬损他的意思。我的推测不过是个荒诞的假设,任何艺术其实本质都是孤独的,这并没有妨碍或阻止我对他的山水画的喜爱。我同他有过多次倾心的交谈,得知他幼时就启蒙古典文学与书法,先后师从当代名家孔仲起、鲁慕迅。曹渔对于山水画自有他的主张:“画当求其‘正、大’,‘正而无邪’、‘大而不雕’者乃可得气象;亦当求其‘清、和’、‘气清韵和’者方可谓入格。凡画,当知‘守常’与‘创变’。‘守’者,‘文化基因’与‘笔墨精神’之‘常’,‘创变’者,笔墨‘体’与‘用’之辩证发展,体貌器格之创立也。凡画,当知‘敛、放’二字。‘敛’者如老僧参禅,‘放’者似处子游春。”他将他的主张始终贯穿于他的作品中。 曹渔的山水画让我怀念起那个盛产诗歌的农耕文明时代。也许那个年代远去了,可我们内心永远存有不灭的幻想。 修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