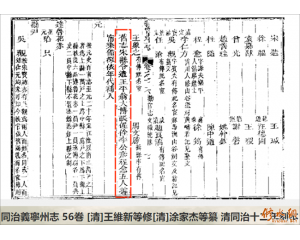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二十年前的今天,我那慈祥善良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解放后,父亲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平平安安过了几年日子。1956年,父亲不甘于农村的平淡生活,在同族一位叔公的帮助鼓励下,带着母亲一同来到刚创办不久的位于太阳升镇的三都垦殖场工作。  修水网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住的是草棚,干的是早晚两头“看星星”。他带领队里的同事从早到晚开垦荒山,把昔日的乱山岗变成了一丘丘的茶地。 当年的三都垦殖场员工少,农家肥也就少,化肥根本谈不上。为了使茶园里的茶树长得快且好,父亲就带领队员利用秋季锄草烧火土灰,冬季就用粪桶从三都镇那边把粪水挑回场茶地里,每一次往返就是七八公里,每天最少八、九个往返。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粮食不够吃,父亲他们就在茶地边种点红薯、挖点野菜补充,实在是不够时,就到附近农村的砖窑厂去刨“观音土”掺野菜吃。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父亲没有退却,继续开山造地。然而此时,我的大哥却不幸患病,经过医生诊断,需要到大医院治疗。 当时的县医院还没有这个技术条件,交通又十分不便,在场领导关心帮助下,父亲决定与母亲一道背着大哥,步行几天几夜绕道南昌就医。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大哥的病趋于好转,父母他们又同样步行回到家。 内容来自xiushui.Net 半年后,父亲在为一位病死的职工当“八仙”时,不小心被压成内伤,年轻时简单吃点药也就挺过去了,但为后来却留下了隐患。  作者父母亲1996年摄于九江火车站 。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已是场委员兼制茶厂的书记。当时场里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之间经常发生互斗。由于父亲在场里为人好,两派都想拉父亲参加,他都一一拒绝。 白天按照上级的安排进行抓革命,晚上又要带领职工把白天采茶工采回来的鲜叶进行加工,往往一做就到下半夜,鲜叶多时就是一个通宵。茶叶在进行烘干抖筛时,灰尘很大,那时的劳保意识也差,时间一长,长年累月不经意就得了肺病。 到了1983年,父亲因积劳成疾又大病一场,这次病彻底把他的身体摧垮了,在县人民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因得的是肺炎、支气管炎、心律不齐等综合并发症,一米七多个头的他瘦成不到80斤。 内容来自xiushui.Net 病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医生说要想彻底好是不可能了,于是父亲就开些口服药回到家里。场里安排父亲在家休息,工资全额发放,可他非要坚持上班,说重体力劳动干不了,搞搞仓库保管是可以的。 就这样,没读过书的他,在五六十岁之时还要我们教他认写一些简单的字,直到退休。期间,父亲每年都因病要到县人民医院最少住一个月的院,久而久之,就连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我们基本都认识了。  1994年作者全家福(后排右二为作者)。 转眼间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五兄弟中最小的也已成家,生活都逐步好起来了,逢年过节回家总要带些吃的东西回去。父亲却舍不得吃用,总念到他生病时别人对他怎么怎么好,要我们把东西你一家他一家地拿去以诚谢意;同时还要我们多到与他同事的老职工家走动看望。 父亲就是一个宁可自己不吃少穿也要做人情的人。我们多次要父母亲来城里住,可他们总以在场里住习惯了为由不来,其实是怕给我们增加“负担”。 本文来自修水网 由于父亲老毛病一直没好,所以每天都要吃大把的药,我们担心他有什么毛病不方便了解,特意花几千元为家里安装了一部座机电话。父亲历来是只接不打,生怕多用我们一分钱,可对待亲戚朋友呢却总是叮嘱再叮嘱,让我们能照顾尽量照顾。 “子欲孝而亲不在”。1999年的冬月,父亲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是个让我们永远伤心的日子。刚好我们做子女的条件好些,他老人家却走了。 在料理父亲善后的过程中,场里近百人来帮忙。父亲在世时我们就在白岭老家为他老人家搭建了“生圹”,原计划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准备运往白岭的,但场里的老同志坚决不同意,说“在场里几十年,不能就这样草草了事,一定要请和尚来好好地为他热闹一下。” 我们顺从了老同志的意思办,第三天场里为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父亲运往白岭。车动之时,场里在家的男女老少都含着眼泪来送别几里。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我时常思念起我的父亲来。他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处世,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挥之不去。 xiushui.Net 二十年了,父亲,您在他乡还好吗?儿子想你了!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