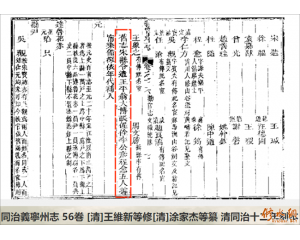蜘蛛在丝线上荡着秋千,但很快就镇定了。它认出了自己,那许多镜子中的自己,虽然看起来每只蜘蛛都不相同,但的的确确就是它自己。让蜘蛛困惑的是,有那么多个自己竟然之前没有发现。惊恐的蜘蛛,悠然自得的蜘蛛,迷惑的蜘蛛,渴望求爱的蜘蛛,肉欲焚身的蜘蛛,赶赴一场约会的蜘蛛,无所事事的蜘蛛,沮丧的蜘蛛,失败的蜘蛛,夏日黄昏饱餐过后的蜘蛛,慵懒的蜘蛛,发过飙后又安静的蜘蛛……蜘蛛从丝线上掉下来,终于抵达地面了,落在其中一块细小的镜子上。它仔细端详镜子中的蜘蛛,那么多个自己,又倏忽不见了。它爬往了另一面镜子,在那面镜子上也找不到那些另类的自己。它很纳闷,这到底怎么了,是谁同它开了这么个玩笑,那些不同的自己又躲到哪儿去了。 xiushui.Net 它又想,消失就消失了吧,毕竟看到这么多个不同的自己了。 又比如我是只土蜂。小时候,到冬天,就会掏土蜂玩。那时候乡村多的是土墙,向西的那面墙被土蜂掏出了许多小洞,也有可能那些墙洞不是土蜂掏的,究竟是谁掏的我现在都没法弄清楚。土蜂都喜欢向西的那面墙,向西,冬天就能晒到一个下午的太阳,墙洞自然温暖。我拿根细小的竹枝,朝墙洞里挠啊挠啊,就有一只土蜂受不了我的骚扰,从墙洞里爬了出来。掏空了一个墙洞,接着掏另一个墙洞,每个墙洞都藏着土蜂,有时一只,有时两只。那么多的土蜂藏在墙洞里,怒气冲冲的土蜂,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的土蜂,不耐烦的土蜂,一脸恐惧的土蜂,被惊扰酣梦的土蜂,伸出脑袋一探究竟的土蜂,嘟嘟嚷嚷的土蜂,愤怒得说不出话的土蜂……每只土蜂的表情都不相同,但最后的结局又都一样,无辜地死亡了,做了我的牺牲品。 后来,就不掏土蜂了。 再往后,我就专注于小说,专注于掏小说中的那些“土蜂”。把他们从小说中掏出来,从现实世界中掏出来,从我的内心掏出来。一个小说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土蜂”。我不停地写,就不停地有陌生的“土蜂”飞进我的世界。他们像我,又不是我,那么多的“土蜂”,那么多的“我”。我对他们似曾相识,可又感觉陌生。我始终被“求变”的狗追赶着。我愿意尝试新的东西,那些我不熟悉的东西,不熟练的东西,小说的手法,结构,语言,进入的角度,内在的空间,饱满度,甚至句式的变化……那么多能说会道的人中间突然走进来一个结巴……所有的小说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流淌的河,上一朵浪花不同于下一朵浪花,此处风景绝不重复彼处,打结巴的地方就是一个漩涡。我无比渴望有一张陌生的脸,一个陌生的角色进入我的小说。我愿意尝试不同的自己,看到不同的自己。把那些隐秘的,埋没的,藏在封闭角落里的自己,挖出来,揪出来,释放出来。把藏在骨髓里的,敲打出来。把细胞核里的,解剖出来。我期望变脸,那么多的脸谱,红脸,黑脸,白脸,生旦净末丑,一张新的脸谱总让人感到惊异。变化到最后,总有终止的时刻。一个没有新鲜事物出现的世界,那将是多么可怕。世界上最乏味的事情,莫过于重复小说中的角色,在两个小说中出现同一张丝毫没有变化的脸,那会叫人多么沮丧和绝望。我祈祷这种倒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HULING 我端坐书桌前,打开电脑。每次我都幻想,正在打开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世界。未知的世界肯定有未知的“土蜂”飞进来。这有些像坐在酒吧间,每个进来的人都不一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挤进酒吧的,是怎样的一张脸。那只刚刚飞进来的“土蜂”,要陌生,要让人惊奇,要有无数未知。就像站在小说的门口,无法抵达,而又必须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