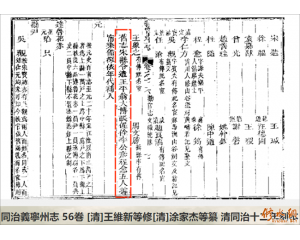七十五年了,老屋看上去依旧是那么坚实,那么雍容。 青砖、黛瓦、马头墙,砖木石雕、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无不诉说着那逝去的辉煌。 老屋是爷爷和奶奶亲手做的。如今,老屋早已没有了她的主人。 上个世纪初,爷爷出生在赣鄱平原上一位普通农民家庭。为了生计,他10多岁就当上了挑夫,每天挑上上百斤的担子要走几十公里路程。还是孩子的他,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汗水和泪水常常沾满爷爷的衣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我曾一次又一次在脑海里构思着爷爷挑着重担,吃力行走的样子,以致于每次在街上遇见挑着重担赶路的人,总要忍不住多看几眼。 25岁那年,爷爷结婚了。奶奶是赣鄱平原上一个小脚女人,她出身在大户人家。为了能将婚礼办得隆重些,爷爷在结婚前一个多月,几乎忘记了休息,拼命地挑着担子挣着工钱,工作量是其他人的两倍多。 HULING 当爷爷用一台大花轿抬着奶奶进门时,奶奶做梦也没想到,爷爷家竟是那么地穷,穷到连住的房屋都不能遮风挡雨。爷爷愧疚地说:“不出五年,我要做一栋村里最漂亮的房子给你住。” 婚后,爷爷的工作更加卖力了,挑着担子越来越重,常常出门几天不回家。 这往后的日子,奶奶带着3个年幼的儿女在家省吃俭用,含辛茹苦,一点一滴积攒着盖房子的钱财。奶奶买来一只咸鱼挂在墙壁上,带着3个儿女扒一口饭,看一眼咸鱼。 终于,老屋在爷爷和奶奶的期盼下动工了。这是他们结婚后的第10年,已远远超过了爷爷5年时间的承诺。1941年初,老屋终于建成了。青砖壁瓦,雕栏玉砌,很是美观,分上下两层,一层建有天井。但那笑容像个老人,完全看不出他只有32岁。 然而,就在那一年,爷爷因积劳成疾,患上了那个年代的不治之症——痨病。医生说,这个病是重担压出来的。1941年夏,爷爷离开了人世。当年,他的小儿子、我的父亲只有5岁,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这屋,是我丈夫用命换来的!” 只有30岁的她从此守寡,艰难地抚养3个儿女成长。 HULING 爷爷安葬在离老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坡下,大跃进年代,那里修建了一座大水库,把爷爷的坟墓淹了,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却远在他乡。多年来,父亲和他的姐姐、哥哥多次试图找到爷爷的墓地,但均没有结果。 2015年夏,父亲80岁生日的时候,带着我们一大家子回到了老家。站在淹没爷爷坟墓的那座水库大坝上,我思绪万千,偌大的水面,沿着大坝一路来回行走,我又想了那个挑着重担、吃力行走、浑身浸透汗水的年轻人来。我知道,眼前这茫茫的水库下面,有我爷爷的坟茔,他一直浸泡在水中,我不知道他32岁的尸骨还能抗击多长时间的雨水侵蚀,我也不知道,他在天之灵是否在责怪他的后人为何不把他“救”出水面,找一个干爽、看得到阳光、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安葬,我更不知道,这往后的岁月里,这种对爷爷的思念,如何走出这种埋在水下、却不能相见的困境。 在老屋前,我抚摸着一块块的青砖,为了省工钱,这些青砖,是爷爷一担一担从远处挑回家的,那上面不仅有我爷爷的手印和汗水,还有他对妻儿的爱念、对家庭的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80岁的奶奶就是在老屋里去世的。老屋见证了我的亲人的生活点滴。 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从老屋的间墙上拿了一块青砖放到各自的车内,我想,爷爷的爱念和责任是要传承下去的。 xiushui.Net 我和父亲、弟弟、儿子在老屋前拍了一张合影。我想,老屋的每一块砖,每一扇门框,每一个雕花都有灵感。爷爷、奶奶一定能够感觉到,因为我坚信,亲情是能通过血液感应的。 告别老屋了,回头张望,老屋就在夕阳下。我突然想起了水木年华那首《老屋》来: 亲爱的老屋,不大的窗户 阳光撒进来,告诉我日落日出 门外的小树,是爱的礼物 …… 亲爱的老屋,还停在原处 而你在哪里,只留给我回忆的幸福 无论你现在何处,我都爱你一如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