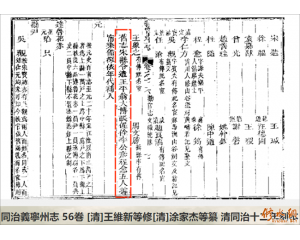|
三月。画舫。一条名叫修水的河流。 我,先是行走在三月的风里,行走在修水的岸边。我同河流只隔了一道浅浅的堤岸。我的手伸出去,它就横亘在河流之上了。软软的风,暖暖的阳光,很快就簇拥在指尖上。但我很少将手伸出去,我怕它一不留神会伤着河流的眼睛,虽然在此之前我将指甲剪干净了,甚至磨平了些微的棱角。 河流是有眼睛的,它的眼睛像镜子一样,明亮,洁净,看不到丝毫的阴霾。它的眼睛里有着蓝蓝的天,洁白的云,飞鸟的掠影,静静的舟楫。一个站在堤岸上的人,只不过是它睫毛上一粒细小的尘埃。风一吹,就有可能落进眼睛里。我因此走得很小心,我怕我会变成它眼睛里的一粒尘土,我怕我阻挡了一条河流的视线。 有时候,我想,我有幸成为河里的一粒沙子,一滴水,或者一尾鱼,一只虾。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这条河就是我一个人的河流了。我可以在河流的任何地方———上游或者下游,奔跑,嬉戏,像鱼一样跳跃。或者像一个疯子一样尖叫,哭泣。黯淡的时光,我就在河床里沉睡,一个人守着一条河,守着自己,让河水洗去满身的污垢,让鱼儿舔净心上的伤口。睡醒了,任由下一轮波浪将我送到岸边,浅滩上,静静地做梦,静静地享受每一缕阳光。慢慢地,这种幻想就变成了我的渴望,一种缘自内心的企盼。 内容来自xiushui.Net 就在三月,我裹挟着一团火焰走近了这条名叫修水的河流,走进了它的怀抱。站在画舫的甲板上,我同它仅仅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它就在我的脚板底下,像一条血管一样汩汩流动。我触摸到了它坚强有力的脉搏,我聆听到了它像海涛一样的心跳。咚咚,像谁在叩打我生命的门板。我感觉到了它的体温,以及它唇边饱满的湿度。它似乎就是我的一个女人,又好像是我的一条血管,河水正从我的心脏里流过。我甚至能捕捉到河水的行走,它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在我的心叶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发现,我竟然如此熟悉这条河流,它同我梦里的那条河流并没有一丝半点的差别。一样的堤岸,一样的河湾,河滩上浅浅的草,天幕上流动的云。那支篙有多长,那支桨有多粗,那条鱼是做了父亲,还是做了祖父,我都知根知底,不用谁来告诉我。还有水面上追逐的两只水鸟,它们哪一天相识,又在哪一天相爱,我都一清二楚,虽然有时它们藏在水草里,故意不让我看见,可我还是认得清哪只低飞的鸟儿是它们的孩子,哪只又不是。它们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这不是梦,不是纸页上的幻想。也许我前生就是一个渔人,在这条河里撒过网,捕过鱼,还向着河水尿尿过。或者我就居住在岸边的某个村庄,从河里引水灌溉我的庄稼,傍晚时刻,我用河水洗干净脚上的泥土,扛起锄头,牵着牛,返回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或许我是一个女人,在河边为我命里的男人浣洗衣纱,为我和他的孩子清洗尿布,淘米洗菜,打草喂猪。委屈的时候,眼泪直接掉进河里,同河水一起悄悄流逝。 HULING 甚至,沿着河岸寻找,还能找见我的脚印,还能看见我在河边小憩时留下的痕迹。我想否认也否认不了,想拒绝却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在岸边的那幢小屋里,我同一个女人相爱过,同她生儿育女,一起白发苍苍,死后我们都被埋葬在河岸边。现在,在河岸的某棵树下,还能挖掘到我们前生未及腐败的骨骼。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有一些骨骼被树吸收了,所以树长得又高又直,它的叶片覆盖在河流之上。 在这条河流之上,也许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单独的自我,而是无数个人的组合,无数个人的重叠。我是祖父,又是父亲,还是别人的孩子。最后,我和他们都回到了河流中央。就像一张纸页,字迹消失,揉皱了,搓烂了,又回到了树的骨头里,回到了叶片上。这是最好的归宿,对于我们又何尝不是。 今天,我坐在画舫之上,拥有了阳光、流水,带着暖意的风,两岸的景色,一条河的宽度和深度。我拥有的,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条河流成了一个空旷的舞台,只有水在静静地流淌。这条名叫修水的河流,我用几把刀子才能将它从我的骨头里剔除,连一丝筋脉也不会留下。我明白我是徒劳的,我找不到这样的刀子。也许世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刀子。我听见一个人的歌声在背后响起,河流里的歌声——— HULING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地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终转;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驱赶不散…… |